塔罗牌愚人(正位/逆位)牌义讲解:
1、原始设计
一位以侧影示人的蓄鬓老者。他笑着,左手捧着一颗球,里头包藏着“幻觉”;而在他的右肩,一柄长463行的柱杖则握在他的右手中。他脚下蹲伏着一头狮子和一条龙,但他对它们的攻击或爱抚似乎毫无所觉。
2、生命之树
路径11,连结(1)“Kether”——王冠,至(2)“Chokmah”——智慧。
3、色彩
明亮的浅黄、天蓝、蓝翡翠绿、洒金斑的翡翠绿。

透特愚人/愚者
哈利斯致克劳利,日期不详:
我将会和“愚人”搏斗一番。他不断扭来扭去,我看不清他。他身边可有小孩?他的袋子是不是弄臣的气球?那份纯真的兴高采烈需要圣人的画笔,而我画出来的线条却像是黏糊糊的糖蜜。但愿我能以水晶来作画。
你可能会感到奇怪,但我将引用克劳利对于最后一张大牌世界的描述,来开启我对第一张塔罗大牌愚人的评论:
因此这张牌本身包含着某种完成的符号,标记着最高意义上之“伟大工作”的完成,正如愚人牌象征着它的开始。愚人是正要流入显化的“负”;而世界则是显化的表现,它的目的已经完成,准备回归。这两张牌之间的二十张牌,则展现“伟大工作”及其媒介之各个不同的阶段。
在本质上,其实并没有二十二张大牌,而只有一张——愚人。所有其他的大牌,都住在愚人之内(并由之释出)。在所有七十八张塔罗牌中,没有比它更受尊崇、也更被误解的了。在《托特之书》中,克劳利用了超过二十四页的篇幅,单单讨论这张牌,此中,他给了我们一趟旋风般的旅行,遍访了希腊、罗马、印度、希伯来和异教神话的重要神衹。
愚人最为人熟悉的形象是一位年轻的流浪汉,头上戴着月桂叶或长春藤编织的花环。他手握一朵白玫瑰,身穿五颜六色的外衣,肩上挑着一根木棒,尾端击着一个袋子或包袱。有时会有一只狗或鳄鱼在啃咬他的脚。他漫不经心地走向悬崖边缘,眼光不负责地投向天空。他一脚仍然踩在实地上,另一脚则作势跨出致命的一步,坠入万丈深渊。哈利斯夫人的愚人则有所不同——他的两只脚都不太稳固地踏在半空中!
为何愚人如此神秘而又令人敬畏?他难道不仅只是中世纪人物卡司中的一员,对着皇帝、皇后和大祭司插科打诨的弄臣?或许吧!这种形象确实符合这张牌许多传统版本的图像。但是从神秘学的观点来看,愚人要比这多得多(事实上,是少很多、很多)。愚人提出了终极的谜题,万物的创生和生命的意义是个难以理解的玩笑。愚人超越了神。他就是“无”,是当我们说,“无”创造了神,“无”超越了神,“无”比神更伟大时,所指的“无”。愚人的脑袋全然空空如也,因为如果里头有任何东西,他的天真便会被摧毁。
作为第一张大阿卡纳牌,愚人被视为第一号牌,是很合乎逻辑的。然而,他却并非第一号牌,他是零号。这是愚人头一个、也是最伟大的戏法——从“无”之中创造出“一”(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其他的一切)。
你的理性头脑在呐喊:“这太疯狂了!”而你的理性头脑是正确的——在某种程度上。“无”中可以生出“有”,这不合理。然而,如果我们要将“无中生有”的非理性概念拟人化,还有什么会比一个不知所谓的傻瓜——也就是愚人——更好的吉祥物呢?
我曾看过好几幅被克劳利打回票的早期草图。令我开心万分的是,我发现其中两幅,确然无误地呈现着喜剧演员哈泼▪马克斯(HarpoMarx)的造型。太贴切了!在马克斯兄弟的电影中,哈泼一向是典型的傻子。即使是哈泼这个名字,都透露了他的真实身份。他不仅仅是那个追逐女孩的小丑,愚弄着所有一本正经、道貌岸然的角色,而且他还从头到尾不发一语。 他沉默不语,就像愚人由之取材建构的那些神话人物;他沉默不语,就像希腊的纯真之神哈泼克拉提斯(Harpocrates);他沉默不语,就像被潘修斯王(Pentheus)询问“何为其理?”的酒神戴奥尼修斯(Dionysus)。
托特塔罗的愚人牌保留了传统塔罗愚人熟知的元素,但也大胆地主张,我们正在处理的人物不是别的,而是每个时代和文化中最不可思议的至上神衹。他是 “春之绿人”;是赢得圣杯的天真傻瓜帕西法尔(Parsifal);是纯真的古埃及寂静之神胡尔▪帕▪克拉特(Hoor-Pa-Kraat),足踏着鳄鱼神——“吞食者”塞贝克(Sebek)。他狂野的双眼、头上的角、脚边的老虎,还有葡萄和藤蔓,显示他是千百年来以戴奥尼修斯之名受人崇拜的宇宙神秘要素——戴 奥尼修斯▪札格列欧斯(Dionysus Zagreus),生着角的宙斯之子;以及巴库斯▪戴弗斯(Bacchus Diphues),醺醉且疯狂泛性(omni-sexual)的神圣狂喜之神。
哈利斯夫人笔下的愚人,是神圣意象的万花筒,其中许多意象要在长久冥思之后(还得借助一面放大镜),才会显现出来。有三道回圈从他的心脏发出,然后又回归到心脏。从这些回圈后面,他迸入存有的半空中。这三道回圈是Ain、Ain Soph,和Ain Soph Aur,也就是喀巴拉学者所教导、肇生出造物之奇迹的“空无之三重帷幕”。他的包袱满满装载着行星及星座的硬币,亦即整个宇宙。
愚人就是圣灵本尊。圣灵的象征白鸽,转化的象征蝴蝶,变幻不定的风之象征“生着翅膀的圆球”,以及古埃及的兀鹰女神姆特(Muat),全都从愚人右手所执的圣杯中涌流而出。如同圣女玛利亚,玛特感应风之圣灵(气息)而受了孕。这整个图像,克劳利告诉我们,便是一一幅创造之光的图形符文。
了解这些之后,最后我想将读者的注意力带到覆盖愚人鼠蹊部位的太阳图形,以及位于鳄鱼头顶、几乎难以看见的月亮图形上。居于这两个原初阴阳象征之间的,是克劳利所谓的“在中央螺旋上相互拥抱的孪生婴儿,上方悬挂着三花合一的赐福”。
对于这些象征符号的意义,我们只能思索推测。在我看来,它们极有可能是在暗示(至少是部分地)炼金术的某些面向,而这是克劳利不太会在出版资料中详细论述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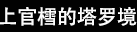 上官樰
上官樰